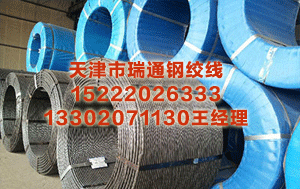汕尾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聊斋故事: 鼠友

海曲县东三十里,有山名贶,山脚下有座早已废弃的山神庙。庙里住着个乞丐,因住在贶山,人们便叫他贶山。谁也不知道他本名叫什么,从何处来,只知道他腿有残疾,走路一瘸一拐,年约三十五六,瘦得只剩一副骨架撑着一张蜡黄的皮。
这年冬天,北风呼啸,大雪下了整整三天三夜。天地间白茫茫一片,路都被积雪埋住了。贶山从集市上乞讨回来,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跋涉。寒风如刀,割在脸上生疼,单薄的破衣根本抵挡不住严寒,他冻得牙齿打颤,浑身哆嗦。
好不容易挪回破庙,他连忙在庙堂中央生起一堆火。火苗蹿起时,他感到一丝久违的暖意。从破布袋里掏出一个黑面馒头——这是今天唯一的收获,他小心翼翼地掰下一小块,正要送入口中,忽然瞥见火堆旁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定睛一看,是只老鼠,个头却比寻常老鼠大得多,几乎有幼猫大小。它浑身湿透,瑟瑟发抖,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正可怜巴巴地望着他手中的馒头。贶山本想挥手赶它走,可看到它那副模样,心中一动——自己不也和这只老鼠一样,在这寒冬里饥寒交迫,无依无靠么?
他叹了口气,掰下一小块馒头渣,轻轻扔过去。老鼠迟疑片刻,慢慢靠近,嗅了嗅,然后小口小口吃起来。吃完后,它没有离开,反而在火堆旁蜷缩成一团,渐渐睡着了。
贶山呆呆看着这场景,心中涌起一股奇特的温暖。这破庙里,除了他自己,终于有了另一个活物。他不再感到那么孤独了。
自此,这只大老鼠便在庙里安了家。贶山每天乞讨回来,总会分它一点食物。有时是馒头渣,有时是半块饼,最难得的时候,还能有几粒米。老鼠似乎也通人性,从不乱碰他的东西,只在角落安静待着,等他回来。
漫长的冬天在相依为命中慢慢过去。冰雪消融,春暖花开,山野间渐渐有了绿意。
村民们开始下地劳作,整地、播种,忙得不亦乐乎。贶山坐在庙门口,默默看着田间忙碌的人们,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想起自己也曾有田有地,有房有家。父母勤劳本分,家中虽不富裕,却也衣食无忧。可恨自己年轻时交了一帮狐朋狗友,学会了赌博,先是输光积蓄,接着抵押田地,最后连祖屋也赔了进去。父母被他活活气死,葬了双亲不久,家乡又闹饥荒,他只好背井离乡,一路乞讨来到此地。
如今看到别人在自家田里辛勤劳作,秋天将会有收成,有盼头,而自己却一无所有,年近四十仍以乞讨为生,心中悔恨如毒蛇啃噬。他摸了摸残疾的右腿——这是三年前乞讨时被恶狗咬伤,无钱医治落下的毛病。因为这腿疾,连去大户人家做短工都没人要。
“我这一生,怕是完了。”他喃喃自语,眼中泛起泪光。
秋天来临,田野金黄,村民们欢天喜地收割庄稼。贶山依然每天下山乞讨,不同的是,如今他有了个伴——那只大老鼠几乎与他形影不离,他出门时,它会送到庙门口;他回来时,它会在门前等候。
然而好景不长。一天早上,贶山醒来,发现老鼠不见了。他在庙里庙外找了一圈,不见踪影,心中顿时空落落的。连续几天,老鼠都没回来,他食不知味,夜不能寐,仿佛失去了唯一的亲人。
这天傍晚,乌云密布,不一会儿便下起了倾盆大雨。贶山无法下山,只好在庙附近摘些野果充饥。夜幕降临时,雨势渐小,他躺在干草堆上,昏昏欲睡。
突然,庙门被推开,一个身着灰衣的男子走了进来。此人身材瘦小,尖嘴猴腮,眼睛又黑又亮,浑身湿透,像只落汤鸡。他看到贶山,咧嘴一笑:“这位兄台,在下路过此地,突遇大雨,可否借贵地避一避?”
贶山久未与人交谈,见有来客,顿时来了精神,忙起身道:“请进请进,这庙也不是我的,兄台不必客气。”
灰衣人自称郝大,家住附近山村。两人围着将熄的火堆坐下,贶山添了些柴,火又旺起来。交谈中,贶山惊讶地发现,郝大似乎对他的事情了如指掌——知道他腿有残疾,知道他每天下山乞讨,甚至知道他最近因为老鼠不见了而郁郁寡欢。
“郝兄如何知道这些?”贶山忍不住问道。
郝大神秘地笑笑,没有回答,转而谈起天气收成。雨停后,郝大告辞离去,临走时说:“贶山兄若有什么困难,可随时找我。”
贶山只当是客套话,并未放在心上。不料三天后,郝大真的来了,还背着一袋粮食。贶山又惊又喜,连连道谢。郝大摆摆手:“一点心意,不必客气。我看兄台日子艰难,能帮则帮。”
此后,郝大每隔几天就会送来粮食,有时是黍,有时是麦,还有菽、稷等各种杂粮。破庙角落里渐渐堆起一座小小的粮山。贶山不再挨饿,脸上渐渐有了血色,身体也壮实了些。
随着交往深入,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郝大性格幽默,见识广博,常讲些奇闻异事逗贶山开心。贶山也将自己的悲惨经历和盘托出,说到痛处,郝大会默默倾听,偶尔叹息。
一天,两人对坐闲聊,贶山忽然长叹一声。郝大关切地问:“兄台为何叹息?身体不适?”
贶山摇摇头:“不是。只是想起已经很久没尝过酒味了。”说完自觉失言,忙补充道,“我就随口一说,郝兄不必在意。”
郝大却笑道:“想喝酒有何难?明日我给兄台带来。”
第二天晚上,郝大果然拎着一坛酒和一只油纸包的烧鸡来了。贶山激动得手都有些发抖——他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喝酒吃肉是什么时候了。两人就着火光,喝酒吃肉,谈天说地,直到深夜。那一晚,贶山醉得畅快汕尾预应力钢绞线价格,睡得香甜。
有了粮食,有了酒肉,贶山的生活改善了许多。然而人的欲望总是水涨船高。一天喝酒时,贶山又叹起气来。
“郝兄,你看这世间,有人锦衣玉食,有人饥寒交迫,命运何其不公!我若是有钱,定要买间房子,置几亩地,安安稳稳过日子。”他醉眼朦胧地说。
郝大闻言,沉默良久,酒喝完便告辞了。贶山以为自己的话得罪了他,心中忐忑。谁知半个月后,郝大深夜来访,将一个沉甸甸的褡裢放在他面前。
贶山打开一看,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,足有上百两。他惊呆了,扑通一声跪下:“郝兄,这、这使不得!”
手机号码:13302071130郝大扶他起来:“这些钱你拿去,买间房子安身吧。只是......”他欲言又止。
“只是什么?郝兄但说无妨。”
郝大有些不好意思:“实不相瞒,我的房子前些日子被大雨冲垮了,如今也无处安身。兄台买了房子,可否留我一间容身?”
贶山一听,当即拍胸脯保证:“郝兄说哪里话!没有你,我哪有今日?我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,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!”
几天后,贶山在离山神庙五里外的村庄买了一座小院,三间正房,两侧厢房,预应力钢绞线虽不豪华,却也整洁宽敞。他用马车将破庙里的粮食全部运回,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家。
郝大住在后院厢房,两人依然经常一起喝酒聊天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贶山看着日渐减少的银两,心中开始焦虑。郝大看出他的心思,建议道:“兄台,坐吃山空终非长久之计。不如用剩下的银子做点小生意,比如当个货郎,或者开间杂货铺。”
贶山觉得有理,便用余钱在村里开了间小杂货铺。出乎意料的是,生意竟十分红火。他腿脚不便,但为人诚恳,价格公道,村民们愿意光顾。不到一年,杂货铺的规模扩大了一倍,贶山也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掌柜。
有钱之后,贶山结交了一些朋友,多是些小商贩和村里较富裕的农户。他们时常聚会饮酒,贶山享受着被人尊称为“贶掌柜”的感觉。渐渐地,他开始觉得郝大是个累赘——这个不事生产、长相怪异的朋友,如今住着他的房子,吃着他的粮食,实在有些说不过去。
郝大似乎察觉到他的变化,主动减少了与他见面的次数,大多时间待在后院很少出来。贶山却越来越不满,常在酒后对朋友抱怨:“我家那郝大,整天游手好闲,白吃白住,真是......”
朋友们劝他:“既是不相干的人,赶走便是。”
贶山有些犹豫,毕竟郝大曾在他最困难时伸出援手。但这种犹豫很快被厌恶取代——特别是当他看到郝大那双过于明亮、似乎能看透人心的眼睛时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不安。
虽然说旭旭宝宝已经是有段时间没有直播玩地下城了,但是对于这游戏的增幅系统宝哥还是非常熟悉的。作为国服第一增幅王,旭旭宝宝这一身增幅18,耳环增幅20的装备也是价值上亿的。而这次回归后宝哥也是开始打算开启又一轮的增幅盛宴了,这次宝哥打算开始冲击红19武器。如果这次宝哥真的成了的话,那么这伤害将会更加的离谱,尤其是等固伤改版转职回狂战士后宝哥的伤害将会出乎大家的意料。不过这游戏的增幅概率是真的非常感人的,之前旭旭宝宝就开启过一次“毁号脱坑”模式,价值上亿的装备全碎了,红19耳环都没了。

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,贶山下定决心要与郝大摊牌。他买了酒菜,来到后院。郝大见他来,很是惊喜,忙收拾桌子。两人对坐饮酒,贶山几次欲言又止。
酒过三巡,贶山终于借着酒意开口:“郝兄,你看我这院子也不大,如今生意上往来人多,后院这厢房我想腾出来存放货物......”
郝大举杯的手停在半空,那双黑亮的眼睛直视贶山,许久才轻声说:“我明白了。兄台容我几日,找到住处便搬走。”
贶山心中一松,连连举杯:“郝兄理解就好,理解就好!来,喝酒!”
两人推杯换盏,不觉都醉倒了,趴在桌上沉沉睡去。
不知过了多久,贶山被夜风吹醒。他揉揉眼睛,正要叫醒郝大回房睡,却猛然僵住了——
月光从窗口洒入,清晰照见桌上趴着的并非郝大,而是一只巨大的老鼠!它穿着郝大的灰衣,戴着郝大的帽子,身躯竟有成年狗那么大!老鼠似乎也醉了,睡得正熟,胡须随着呼吸轻轻颤动。
贶山吓得魂飞魄散,连连后退,撞翻了凳子。巨响惊醒了老鼠,它抬起头,那双黑溜溜的眼睛困惑地望着贶山,竟口吐人言:“兄台,怎么了?”声音正是郝大的!
“妖、妖怪!”贶山尖叫着冲出房门,从厨房抓起菜刀,再冲回后院时,那老鼠精已摇摇晃晃站起身,似乎还没完全清醒。
“兄台,你拿刀做什么?”它用人声问道,声音里带着困惑和一丝悲伤。
贶山哪还听得进去,恐惧转化为暴怒,挥刀就砍。老鼠精试图躲避,但醉意未消,动作迟缓,被贶山连砍数刀,倒在血泊中,渐渐现出原形——一只巨大的灰毛老鼠,穿着人的衣服,场面诡异骇人。
贶山瘫坐在地,喘着粗气,许久才敢上前查看。确认老鼠精已死,他连拖带拽,将尸体拖到村外乱坟岗,草草掩埋。回到家,他清洗了后院血迹,却洗不去心中的恐惧。那一夜,他睁眼到天明。
接下来的日子风平浪静。贶山对外只说郝大回乡去了。他渐渐放下心来,甚至有些得意——自己除掉了一个妖怪,为民除害。
直到一个月后,他在茶馆听说了一件事:村里王大户三个月前走夜路时丢了一个褡裢,里面有一百多两银子;同时,好几户村民地里丢失粮食,都是些黍、麦、菽、稷之类,奇怪的是,贼人似乎只偷一点点,每家丢得都不多,但加起来数量可观。
贶山听得心惊肉跳——郝大送他的粮食和银子,不正是这些吗?他这才明白,那些“馈赠”全是偷来的!若是被人发现,他就是窝赃,要坐牢的!
恐惧再次攫住了他。他暗自庆幸自己及时除掉了老鼠精,同时严严实实地保守这个秘密,对谁也不提。
一年后的一个傍晚,贶山与一位往来密切的布商朋友喝酒。酒酣耳热之际,朋友叹道:“贶兄能从一贫如洗到今日小康,真是运气好啊!”
贶山已有七分醉,闻言得意起来,压低声音说:“不瞒你说,我能有今天,多亏了一位‘朋友’相助......”便将郝大的事含糊说了,虽未明说是老鼠精,但暗示“那位朋友不是常人”。
朋友听得面色大变,匆匆告辞。贶山酒醒后,隐隐觉得不安,但安慰自己不过是酒后胡言,朋友未必当真。
第二天一早,贶山还在睡梦中,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开门一看,竟是三名衙役!
“贶山,有人告你与数月前王大户失窃案有关,跟我们去衙门走一趟!”
公堂上,县令惊堂木一拍:“贶山,有人告你勾结妖邪,窃取钱财粮食,可有此事?”
贶山吓得瘫软在地,不用上刑便全招了,将郝大如何送粮送银,自己如何发现它是老鼠精,如何将其杀死埋尸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
堂上堂下闻言哗然。县令皱眉:“荒唐!哪有什么老鼠成精!分明是你偷盗后编造谎言!来人,让他带路去寻那老鼠尸首,若寻不见,大刑伺候!”
贶山带着衙役和众多村民来到乱坟岗,指着一处地方:“就是这里,我亲手埋的。”
众人开挖,挖地三尺,却只见泥土石块,哪有老鼠尸体?贶山傻眼了,扑到坑边:“不可能!明明就在这里!我亲手埋的!”
县令冷笑:“看来不用刑你是不招了!”
贶山百口莫辩,连连磕头:“大人明鉴!小人说的句句属实!那老鼠精定是......定是逃了!或者被野狗刨吃了!”
因为没有确凿证据,加上村里几位老者为贶山作保,说他这一年安分守己,县令最终将他打了二十大板,释放回家。
贶山拖着伤躯回到家中,对告密的朋友恨之入骨,断然绝交。此事虽未让他入狱,却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。有人说他编造故事掩盖偷窃,有人说他真的遇见了妖怪,更多人则与他疏远,觉得他不祥。
杂货铺的生意一落千丈。贶山整日疑神疑鬼,总觉得暗处有双眼睛在盯着他。他开始酗酒,生意无心打理,积蓄渐渐耗尽。
两年后的一个清晨,有村民在村口老槐树下发现了贶山的尸体。他仰面倒地,眼睛瞪得极大,脸上凝固着极度惊恐的表情,身上却没有明显伤痕。仵作验尸,说是突发急病身亡。
村里人凑钱将他草草葬了。下葬那天,几个老人摇头叹息:“若是当年他能知足感恩,不起恶念,或许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”
有人说,贶山下葬后的连续七个夜晚,村口老槐树下总有窸窸窣窣的声音,像是许多小爪子跑过。还有夜归的村民声称,在月光下看到一只巨大的老鼠影子蹲在贶山坟头,一动不动,直到天明才消失。
但这些传言渐渐随风而散汕尾预应力钢绞线价格,贶山和他的老鼠朋友的故事,最终成了海曲县流传的诸多奇谈中的一个,真真假假,再无人深究。只有那座曾经住过一丐一鼠的破庙,在岁月中彻底倒塌,化为尘土,仿佛从未有过那段奇异而悲哀的缘分。
-

- 01-08

- 查看更多
-

- 12-24

- 查看更多
-

- 12-31

- 查看更多
-

- 12-26

- 查看更多
-

- 12-30

- 查看更多